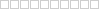创新,就是把“不可能”化为“可能”
来源:物理ok网
编辑:网友
时间:2015-12-02
点击量:次
创新,就是把“不可能”化为“可能”(1.01)
——中国首届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深度推介项目之合学教育
公益博览会时段:2015年12月4号到7号(周五至周一)
公益博览会地点:北京师范大学体育馆(主会场)及院内的邻近场馆(分会场)
合学教育项目汇报提纲:
1.0版:个人层面的十余年探索
2.0版:签约实验校的三年实践
3.0版:托管实验校的未来构想
今天发表的文章,是1.0版的第1篇文章,所以在总标题的后面标注了(1.01),说的是合学教育的主创人员之一李景龙的一段个人阅历。
首先是亲自学习,然后才能找到学习的感觉,进而才能研究学习,并应用学习科学的成果。所以,合学教育的源头,是对于学生学习的体验与关注。
曾经的个案:学习改变命运
李景龙
走出沟谷
山很高,村子很小,颇有坐井观天之感。
弟弟后来在北大电子系读博士时回忆,他是在超过了10岁时才爬上山顶的,当他发现山外还有山、还有天、还有村庄和人家时,颇感惊奇。因为,他不曾听说,更不曾见过山外的世界。
爱人第一次来我们家里,是徒步翻过了那座山的,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。她做了一个浪漫的假设:如果在山顶坐上一辆滑车,那么滑到底端便到了我的家。
在一个三面环山的盆地,找到书、找到读书人很不容易。记得农村过年有用旧报纸、旧书纸糊屋子的习俗,好比是现在给墙壁刷浆。墙壁上的旧报纸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视窗,在那堆旧书中,我还“抢救”了一本俄语书。现在想来,当年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捧着那本俄语书想方设法地去解读,那是怎样的愚笨!但周围没有人能告诉我外语该学什么、怎么学;也没有人能告诉我,外语不经过启蒙是不能自学的。记得我在读初中时就做起了大学梦,可同班同学说,考大学要会7门外语,他们是从村里的民办教师那里听说的,这或许也是我抢救那本俄语书的原因。后来读高中了,我才知道不是会7门外语,而是从7门外语中选择一种。在家里读书,遇到不懂的词、不会的题,很难在方圆几里的范围内找到明白人,只记得因式分解的十字相乘法是向下个年级的学弟学会的。所以,爸爸从县城里买来《三角函数》、《解析几何》,我从上海邮来数理化自学丛书,这样的“硬骨头”,我怎样也啃不动。
农闲的时候,唱几台大戏是农村的娱乐,我躲在小屋里读书显得不入世俗,并由此引来讥笑,但我还是坚持做自己最该做的事情。
学习改变命运,学习也能创造奇迹。公元1982年——建国后第33年,我所在的村庄出了第一个大学生,这使得我有机会获得高层次的、正规的学习机会,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命运的沟谷。
比学生更勤奋
自读书以来,读得最透、揉得最烂的书是报考公务员时用过的。公务员考试主要考文科知识,学理科的我和十多个学文科的考生去竞争一个岗位,能够在竞争中获胜,不是由于天分,而是由于勤奋。
报考公务员时,我更留恋自己的教师岗位。从教的第二年,我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书,名为《学习过程36计》。书是在面向学生的思考中酝酿、在面向学生的反复宣讲中形成的,学生的表情告诉我,他们喜欢我讲的内容。遗憾的是,书在出版社辗转了7年才最终成为一个合法的出版物。写书的日子,全社会尊师重教;出书的日子,知识价值被跌入低谷。所以,我出的那本书连同发表的教学论文并不曾改变我的命运。农村中学的五年教龄是值得珍惜的,它使我在意志上再次得到砥砺,难过的甚至可怕的,是那期间的两地分居。儿子即将分娩的日子,爱人住在另一所学校的单身宿舍,身边没有亲人。这本身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一种我们从没听说过的病导致她产前昏迷,她从床上滚落到地上,炉子烧伤了她的大腿,她痛苦的呻吟惊醒了隔壁的同事。爱人是在同事的护送下进入医院的,当我进入医院的时候,儿子出生了,妻子却住进了烧伤科病房。
那段日子是可怕的,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可怕。如果不是好心的同事伸出援助之手,我们的家庭早已经在灾难中破碎。
命运不因为期盼改变,却因拼争而逆转。报考公务员,不是因为我不爱自己的教师岗位,而是因为那是我解决两地分居的手段。应考的复习资料被揉烂了,书不知被翻过了多少遍。我敢说,在那段日子,我比所在学校的任何一个学生都勤奋。
学习再度改变命运。“吃书”的日子结出的果实,重要的不在于我成为教育局的公务员,而在于我成功地解决了两地分居。
“留学”在兴发
从教师到教育局干部再到县报编辑记者,我是在学习中变通、应对的。在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二个年头,我就获得了全国县市报好新闻二等奖,但事业的发展不能够改变经济上的实力。入不敷出的日子,酝酿着一场爆发,酝酿着一场“穷则思变”的蜕变。此间,让我留恋的是在草原兴发的日子。
我们夫妇俩各自走出了自己的村落,但我们依旧是农家的孩子。读完大学,帮弟弟、妹妹完成学业,我们责无旁贷;母亲患肝硬化长达6年,我们的月工资有时只能支付医院开出的两支蛋白。无力回天,我们送母亲安详地离去。儿子5周岁了,当他趴在墙头上看邻居家的电视时,他哪里知道这样回伤害家里的自尊。面队此情此景,我们做父母的几乎心碎。拥有一台电视,对于工薪族来说不算奢求,但当我们搬回一台属于自己的黑白电视时,已是参加工作后的第8个年头。
就在下海的人有了几分厌倦,或是商界的晴雨表启迪人们纷纷上岸的时候,我下海了——义无返顾、毅然决然,尽管是一介书生、一贫如洗。那时候,我对商界的事情一无所知,只知道自己作为一个“无产者”,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。从“无冕之王”到底层商贩,从一贫如洗到全面亏损,从昔日的朋友到上门追讨“利息的利息”,世态炎凉,尽收眼底。庆幸的是,经过了同伴欺骗、捉弄甚至是极端化的步步紧逼之后,我没在那个心脏急促跳动的瞬间猝死。
危难之中不但不分手反而相濡以沫的夫妻是患难夫妻。家难当头的日子,我们的婚姻质量得到了检验并得到了提升。绝望的时候,爱人把我招回家——那个虽然很破落但又很温暖的家。身心逐步恢复的日子,爱人把她读过的《初来香港的人》讲给我,告诉我从零做起甚至是从负数做起。于是,在经商失败后,我选择了打工。
在上市公司草原兴发工作的日子,我近距离地接触了总经理张振武。我惊奇地发现,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大企业家和坑蒙拐骗的不法商贩之间,原来不是层次的差别,而是门类的不同,正所谓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”。与惟利是图的商贩在一起,如坐针毡;与关注民族、民生的企业家在一起,如临春风。为了发展这家集体企业,张振武总经理有时把睡眠安排在外出的列车上,治病输液也是安排在夜间。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,我真的体会到人格比金钱宝贵许多。在尊重人才的企业,我找回的应有的自尊,得到了应有的礼遇。短短的几个月,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、永久的。我写的《留学在兴发》、《为月薪300元流泪》,在公司报纸发表后,极大地鼓舞了职工的士气;我主持拍摄的专题片《田野壮歌》、撰写的人才招聘宣言《我们的人才观》成为公司的经典之作。我的工资超过了总经理,让我如履薄冰。
说“留学”在兴发是丝毫也不过分的,因为这样的体验式学习是学校里的学习所不能替代的。那段日子,使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人生理念:做人要做有益于别人的人,做事要做堂堂正正的事。我还认识到,一个人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,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做什么,而在于以什么态度去做,做到什么程度。这一点,对于我后来的“个体讲学”来说,是一个良好的精神铺垫。
弄斧到班门
华罗庚学生说过“下棋找高手,弄斧到班门”,讲的是求学之道、成材之道。我的成长经历,也引证了华先生的真知灼见。
第一次班门弄斧,是在刚刚走上讲坛的时候。如果把工作了十几年、几十年的前辈比做“识途老马”的话,那么刚刚走上讲台的我只能算是“初生牛犊”。按理说,当老教师们都纷纷自谦,惟恐言语不当,不愿意写下一点东西的时候,我贸然地张扬自己要写一种叫做“书”的东西,那是对前辈长期劳动的极大的不恭。但我没有不恭的意思,我只是采用了“班门弄斧”学习法,在能人面前、在有资历的人面前做了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向周围的老师们借书,请他们评点自己的书稿,请他们光临自己面向学生举办的学习方法讲座。他们的鼓励与批评催生了我的《学习过程36计》,他们的肯定使得我有勇气把书稿递给了出版社,他们的认同使得我在书稿被压的2000多个日子里没有失去自信。
第二次班门弄斧,是在离开草原兴发日子。当我没有任何“外包装”,以自然人的身份去某重点中学兜售自己的书的时候,没有名家的“签名售书”,没有名字前面一连串的修饰语和那些与身份价对应的“讲课费”,有的只是“免费试听,购书自愿”。在一所当地有名的重点中学,书没卖出多少,但评价却令人鼓舞。校领导说:“你讲的质量并不亚于学校耗资千余元从北京请来的专家”。我知道,他不是在奉承我,因为他没有奉承的必要。不亚于专家,就要当专家,我做起了专家梦。所不同的是,我不拿工资,做的是“个体科研”、“个体讲学”,以一个 “独行侠”的姿态班门弄斧,闯名校,访名师,传播学习科学,造福莘莘学子,并为此获取几分薪水。此间,我创作了《学会学习——中学生学习方法》一书并迅速出版,该书以独立的知识产权成为我“个体讲学”的个人名片。
第三次班门弄斧,是在全国学习科学研讨会的大会发言席上。1996年10月20日,全国学习科学研讨会在天津教科院召开,在与会的大约300名代表中,我是惟一的“个体讲学人”。独特的身份、独特的认识视角、独特的行为方式,使得我被推到了大会发言席。行家看门道,与会代表发现,学习科学研究的“倒立的金字塔”被我翻转了180度,抽象的变为具体,枯燥的变为生动,“可亲、可感、可行”的鲜活特色使得我那15分中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会下,代表门抢购我的书,询问我的联系方式。后来,经市人事局批准,我被破格调入天津,举家一同迁入。据办事人员介绍,市人事局每年从外地调入的人才都有严格的规格限制和指标限制。所谓“规格”,指的是高科技人才,而高级人才的标志之一就是高级职称。当时,我是无单位、无职称、无挂靠的“三无人员”。这里,当然应该感谢天津兴国学校老校长郑秉洳先生的赏识与吸纳。老校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曾任河西区教育局长、津南区教育局长、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等职。老校长半个世纪积累的威望,他为光大事业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打动了区政府、打动了市人事局。据说,老校长用来说明我是人才的证据之一,就是我在那次在会议上被抢购的那本书。
一个寒冷的冬日,我们选择了一个上好的西瓜,准备送给老校长,试图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那天,我们走进了老校长的屋里,东西却被隔离在门外。老校长早年参加革命工作,官至副局级,洁身自好,初衷不改。他说:“把东西带走,是对我为人的尊重。”先生一贯重公众事业、轻个人财产,他全家为兴国学校捐献财务总量达17万元。他致力于学习学研究,首倡学习教育,他团结同仁,提携后进,为的是一种崇高的职业理想。
在学习科学的研究者董国华看来,近来30多年间,中国学习科学在应用层面迈出过三大步:一是以北京八中原校长龚正行为代表的学法指导学派(亦称“京派”),二是以上海教育学院为代表的学习指导学派(沪派),三是以南开大学郑秉洳先生为代表的学习教育学派(津派)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郑秉洳先生就明确提出“以学习科学为指导,推行学习教育;以学习教育为主线,进行整体改革”。作为先生认可的门生,他对于我们寄托厚望。
我们于2008年出版的《合学教育:打造教学动车组》一书,其最初的名称是《合作学习:打造教学动车组》。丛书主编王增昌老师认为,当时合作学习已经很泛滥,已经鱼目混珠。他建议,在书名中适当规避一下“合作学习”字样。就在这一关头,我们的导师郑秉洳先生关切地把我们的工作命名为“合学教育”,并撰文指出:合学教育,其实是学习教育流派的一个分支,一个深化。
饮水思源,我们深切感激郑秉洳先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给予的教导与抚慰。
遗憾的是,先生于2010年3月5日不幸去世。在合学教育不断发展的情况下,研读郑先生的著作,重温郑秉洳先生的期待,我们感到自己任重道远。
(李景龙,1963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大物理系。曾任高中物理教师、教育局干部、新闻记者、学报编辑,曾经在上市公司从事宣传策划,也曾“个体讲学”。1997年被破格调入天津,2009年调入北京。在断续的教育工作与研究中,发表相关文章100余篇,和张素兰老师一起出版了研究学习学的专著《好方法胜过好老师》,出版了体现合作学习升级版的专著《合学教育:打造教学动车组》,《合学教育:突破合作学习的5大瓶颈》,出版了关于优化学案的专著《问题引领:专业课堂的操作平台》。另外,《合学教育:合作学习的升级版》即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。)
——中国首届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深度推介项目之合学教育
公益博览会时段:2015年12月4号到7号(周五至周一)
公益博览会地点:北京师范大学体育馆(主会场)及院内的邻近场馆(分会场)
合学教育项目汇报提纲:
1.0版:个人层面的十余年探索
2.0版:签约实验校的三年实践
3.0版:托管实验校的未来构想
今天发表的文章,是1.0版的第1篇文章,所以在总标题的后面标注了(1.01),说的是合学教育的主创人员之一李景龙的一段个人阅历。
首先是亲自学习,然后才能找到学习的感觉,进而才能研究学习,并应用学习科学的成果。所以,合学教育的源头,是对于学生学习的体验与关注。
曾经的个案:学习改变命运
李景龙
走出沟谷
山很高,村子很小,颇有坐井观天之感。
弟弟后来在北大电子系读博士时回忆,他是在超过了10岁时才爬上山顶的,当他发现山外还有山、还有天、还有村庄和人家时,颇感惊奇。因为,他不曾听说,更不曾见过山外的世界。
爱人第一次来我们家里,是徒步翻过了那座山的,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。她做了一个浪漫的假设:如果在山顶坐上一辆滑车,那么滑到底端便到了我的家。
在一个三面环山的盆地,找到书、找到读书人很不容易。记得农村过年有用旧报纸、旧书纸糊屋子的习俗,好比是现在给墙壁刷浆。墙壁上的旧报纸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视窗,在那堆旧书中,我还“抢救”了一本俄语书。现在想来,当年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捧着那本俄语书想方设法地去解读,那是怎样的愚笨!但周围没有人能告诉我外语该学什么、怎么学;也没有人能告诉我,外语不经过启蒙是不能自学的。记得我在读初中时就做起了大学梦,可同班同学说,考大学要会7门外语,他们是从村里的民办教师那里听说的,这或许也是我抢救那本俄语书的原因。后来读高中了,我才知道不是会7门外语,而是从7门外语中选择一种。在家里读书,遇到不懂的词、不会的题,很难在方圆几里的范围内找到明白人,只记得因式分解的十字相乘法是向下个年级的学弟学会的。所以,爸爸从县城里买来《三角函数》、《解析几何》,我从上海邮来数理化自学丛书,这样的“硬骨头”,我怎样也啃不动。
农闲的时候,唱几台大戏是农村的娱乐,我躲在小屋里读书显得不入世俗,并由此引来讥笑,但我还是坚持做自己最该做的事情。
学习改变命运,学习也能创造奇迹。公元1982年——建国后第33年,我所在的村庄出了第一个大学生,这使得我有机会获得高层次的、正规的学习机会,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命运的沟谷。
比学生更勤奋
自读书以来,读得最透、揉得最烂的书是报考公务员时用过的。公务员考试主要考文科知识,学理科的我和十多个学文科的考生去竞争一个岗位,能够在竞争中获胜,不是由于天分,而是由于勤奋。
报考公务员时,我更留恋自己的教师岗位。从教的第二年,我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书,名为《学习过程36计》。书是在面向学生的思考中酝酿、在面向学生的反复宣讲中形成的,学生的表情告诉我,他们喜欢我讲的内容。遗憾的是,书在出版社辗转了7年才最终成为一个合法的出版物。写书的日子,全社会尊师重教;出书的日子,知识价值被跌入低谷。所以,我出的那本书连同发表的教学论文并不曾改变我的命运。农村中学的五年教龄是值得珍惜的,它使我在意志上再次得到砥砺,难过的甚至可怕的,是那期间的两地分居。儿子即将分娩的日子,爱人住在另一所学校的单身宿舍,身边没有亲人。这本身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一种我们从没听说过的病导致她产前昏迷,她从床上滚落到地上,炉子烧伤了她的大腿,她痛苦的呻吟惊醒了隔壁的同事。爱人是在同事的护送下进入医院的,当我进入医院的时候,儿子出生了,妻子却住进了烧伤科病房。
那段日子是可怕的,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可怕。如果不是好心的同事伸出援助之手,我们的家庭早已经在灾难中破碎。
命运不因为期盼改变,却因拼争而逆转。报考公务员,不是因为我不爱自己的教师岗位,而是因为那是我解决两地分居的手段。应考的复习资料被揉烂了,书不知被翻过了多少遍。我敢说,在那段日子,我比所在学校的任何一个学生都勤奋。
学习再度改变命运。“吃书”的日子结出的果实,重要的不在于我成为教育局的公务员,而在于我成功地解决了两地分居。
“留学”在兴发
从教师到教育局干部再到县报编辑记者,我是在学习中变通、应对的。在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二个年头,我就获得了全国县市报好新闻二等奖,但事业的发展不能够改变经济上的实力。入不敷出的日子,酝酿着一场爆发,酝酿着一场“穷则思变”的蜕变。此间,让我留恋的是在草原兴发的日子。
我们夫妇俩各自走出了自己的村落,但我们依旧是农家的孩子。读完大学,帮弟弟、妹妹完成学业,我们责无旁贷;母亲患肝硬化长达6年,我们的月工资有时只能支付医院开出的两支蛋白。无力回天,我们送母亲安详地离去。儿子5周岁了,当他趴在墙头上看邻居家的电视时,他哪里知道这样回伤害家里的自尊。面队此情此景,我们做父母的几乎心碎。拥有一台电视,对于工薪族来说不算奢求,但当我们搬回一台属于自己的黑白电视时,已是参加工作后的第8个年头。
就在下海的人有了几分厌倦,或是商界的晴雨表启迪人们纷纷上岸的时候,我下海了——义无返顾、毅然决然,尽管是一介书生、一贫如洗。那时候,我对商界的事情一无所知,只知道自己作为一个“无产者”,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。从“无冕之王”到底层商贩,从一贫如洗到全面亏损,从昔日的朋友到上门追讨“利息的利息”,世态炎凉,尽收眼底。庆幸的是,经过了同伴欺骗、捉弄甚至是极端化的步步紧逼之后,我没在那个心脏急促跳动的瞬间猝死。
危难之中不但不分手反而相濡以沫的夫妻是患难夫妻。家难当头的日子,我们的婚姻质量得到了检验并得到了提升。绝望的时候,爱人把我招回家——那个虽然很破落但又很温暖的家。身心逐步恢复的日子,爱人把她读过的《初来香港的人》讲给我,告诉我从零做起甚至是从负数做起。于是,在经商失败后,我选择了打工。
在上市公司草原兴发工作的日子,我近距离地接触了总经理张振武。我惊奇地发现,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大企业家和坑蒙拐骗的不法商贩之间,原来不是层次的差别,而是门类的不同,正所谓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”。与惟利是图的商贩在一起,如坐针毡;与关注民族、民生的企业家在一起,如临春风。为了发展这家集体企业,张振武总经理有时把睡眠安排在外出的列车上,治病输液也是安排在夜间。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,我真的体会到人格比金钱宝贵许多。在尊重人才的企业,我找回的应有的自尊,得到了应有的礼遇。短短的几个月,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、永久的。我写的《留学在兴发》、《为月薪300元流泪》,在公司报纸发表后,极大地鼓舞了职工的士气;我主持拍摄的专题片《田野壮歌》、撰写的人才招聘宣言《我们的人才观》成为公司的经典之作。我的工资超过了总经理,让我如履薄冰。
说“留学”在兴发是丝毫也不过分的,因为这样的体验式学习是学校里的学习所不能替代的。那段日子,使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人生理念:做人要做有益于别人的人,做事要做堂堂正正的事。我还认识到,一个人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,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做什么,而在于以什么态度去做,做到什么程度。这一点,对于我后来的“个体讲学”来说,是一个良好的精神铺垫。
弄斧到班门
华罗庚学生说过“下棋找高手,弄斧到班门”,讲的是求学之道、成材之道。我的成长经历,也引证了华先生的真知灼见。
第一次班门弄斧,是在刚刚走上讲坛的时候。如果把工作了十几年、几十年的前辈比做“识途老马”的话,那么刚刚走上讲台的我只能算是“初生牛犊”。按理说,当老教师们都纷纷自谦,惟恐言语不当,不愿意写下一点东西的时候,我贸然地张扬自己要写一种叫做“书”的东西,那是对前辈长期劳动的极大的不恭。但我没有不恭的意思,我只是采用了“班门弄斧”学习法,在能人面前、在有资历的人面前做了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向周围的老师们借书,请他们评点自己的书稿,请他们光临自己面向学生举办的学习方法讲座。他们的鼓励与批评催生了我的《学习过程36计》,他们的肯定使得我有勇气把书稿递给了出版社,他们的认同使得我在书稿被压的2000多个日子里没有失去自信。
第二次班门弄斧,是在离开草原兴发日子。当我没有任何“外包装”,以自然人的身份去某重点中学兜售自己的书的时候,没有名家的“签名售书”,没有名字前面一连串的修饰语和那些与身份价对应的“讲课费”,有的只是“免费试听,购书自愿”。在一所当地有名的重点中学,书没卖出多少,但评价却令人鼓舞。校领导说:“你讲的质量并不亚于学校耗资千余元从北京请来的专家”。我知道,他不是在奉承我,因为他没有奉承的必要。不亚于专家,就要当专家,我做起了专家梦。所不同的是,我不拿工资,做的是“个体科研”、“个体讲学”,以一个 “独行侠”的姿态班门弄斧,闯名校,访名师,传播学习科学,造福莘莘学子,并为此获取几分薪水。此间,我创作了《学会学习——中学生学习方法》一书并迅速出版,该书以独立的知识产权成为我“个体讲学”的个人名片。
第三次班门弄斧,是在全国学习科学研讨会的大会发言席上。1996年10月20日,全国学习科学研讨会在天津教科院召开,在与会的大约300名代表中,我是惟一的“个体讲学人”。独特的身份、独特的认识视角、独特的行为方式,使得我被推到了大会发言席。行家看门道,与会代表发现,学习科学研究的“倒立的金字塔”被我翻转了180度,抽象的变为具体,枯燥的变为生动,“可亲、可感、可行”的鲜活特色使得我那15分中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会下,代表门抢购我的书,询问我的联系方式。后来,经市人事局批准,我被破格调入天津,举家一同迁入。据办事人员介绍,市人事局每年从外地调入的人才都有严格的规格限制和指标限制。所谓“规格”,指的是高科技人才,而高级人才的标志之一就是高级职称。当时,我是无单位、无职称、无挂靠的“三无人员”。这里,当然应该感谢天津兴国学校老校长郑秉洳先生的赏识与吸纳。老校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曾任河西区教育局长、津南区教育局长、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等职。老校长半个世纪积累的威望,他为光大事业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打动了区政府、打动了市人事局。据说,老校长用来说明我是人才的证据之一,就是我在那次在会议上被抢购的那本书。
一个寒冷的冬日,我们选择了一个上好的西瓜,准备送给老校长,试图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那天,我们走进了老校长的屋里,东西却被隔离在门外。老校长早年参加革命工作,官至副局级,洁身自好,初衷不改。他说:“把东西带走,是对我为人的尊重。”先生一贯重公众事业、轻个人财产,他全家为兴国学校捐献财务总量达17万元。他致力于学习学研究,首倡学习教育,他团结同仁,提携后进,为的是一种崇高的职业理想。
在学习科学的研究者董国华看来,近来30多年间,中国学习科学在应用层面迈出过三大步:一是以北京八中原校长龚正行为代表的学法指导学派(亦称“京派”),二是以上海教育学院为代表的学习指导学派(沪派),三是以南开大学郑秉洳先生为代表的学习教育学派(津派)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,郑秉洳先生就明确提出“以学习科学为指导,推行学习教育;以学习教育为主线,进行整体改革”。作为先生认可的门生,他对于我们寄托厚望。
我们于2008年出版的《合学教育:打造教学动车组》一书,其最初的名称是《合作学习:打造教学动车组》。丛书主编王增昌老师认为,当时合作学习已经很泛滥,已经鱼目混珠。他建议,在书名中适当规避一下“合作学习”字样。就在这一关头,我们的导师郑秉洳先生关切地把我们的工作命名为“合学教育”,并撰文指出:合学教育,其实是学习教育流派的一个分支,一个深化。
饮水思源,我们深切感激郑秉洳先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给予的教导与抚慰。
遗憾的是,先生于2010年3月5日不幸去世。在合学教育不断发展的情况下,研读郑先生的著作,重温郑秉洳先生的期待,我们感到自己任重道远。
(李景龙,1963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198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大物理系。曾任高中物理教师、教育局干部、新闻记者、学报编辑,曾经在上市公司从事宣传策划,也曾“个体讲学”。1997年被破格调入天津,2009年调入北京。在断续的教育工作与研究中,发表相关文章100余篇,和张素兰老师一起出版了研究学习学的专著《好方法胜过好老师》,出版了体现合作学习升级版的专著《合学教育:打造教学动车组》,《合学教育:突破合作学习的5大瓶颈》,出版了关于优化学案的专著《问题引领:专业课堂的操作平台》。另外,《合学教育:合作学习的升级版》即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。)
相关文章:
相关推荐:
网友评论:

说点什么吧……
- 全部评论(0)
还没有评论,快来抢沙发吧!
栏目分类
最新文章